[摘要]人烟,这两个汉字组合得很妙——有人就有烟,“人烟稠密”还可形容市井繁华。现在变了,烟雾成为污染物。北京市民也从家家一炉火,取暖做饭烧开水,生火封火倒炉灰,迅速减少用火,主要用电。
老百姓过日子“开门七件事: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“柴”字打头——总是先给炉灶生火,然后才烧水、做饭、沏茶。那么几十年前北京人常说的“取灯、火镰、洋火、火柴”,是同一种东西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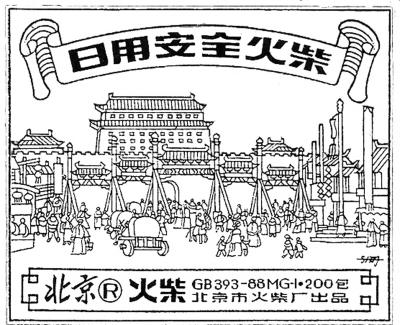
最早学会用火的北京土著,大概就是周口店“山顶洞人”,被考古学家命名为“北京人”。他们居住的山洞里积存着远古时代燃烧过的草木灰烬层——学会用火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。“北京人”用火主要是取暖,熟食,驱逐野兽。熟食扩大了食物来源,人体吸收多种营养,促进大脑发达,成为“万物之灵”。
火种从何而来?古希腊神话传说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堂偷来的。其实地球上火山喷发和雷电也会引燃山林大火,只是人们取火的机会太少,保存火种也很难。中国古老传说是燧人氏“钻木取火”——用木棍在木头上钻出火来——不靠天火,靠发明创造,摩擦生热、起火,完全符合物理、化学。
与“钻木取火”原理相同,中国人又创造了“火镰打火”。火镰形如马掌铁,击打火石(燧石),溅出火星引燃火绒(芦花等草毛),再引燃细长的松木条——用它点灯,所以叫“取灯”。也有人把这一套复杂的取火动作统称为“取灯”。北京人生火、用火,离不开“取灯”。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京郊农民还用火镰打火,点柴灶,烧火炕。抗战时期贵州农家屋里有火塘,烤火、煮饭、保存火种,用竹篾片从火塘里引火点灯。湖南人、四川人吸水烟,也是火镰打火,引燃草纸卷成的细长纸篾子,如同香火缓慢燃烧,对着香火头“噗”一口气,就燃起火苗,点燃水烟袋的烟丝,再吹灭火苗,纸篾子继续缓慢燃烧,可多次点烟,点灯,这是南方人的“取灯”。
一些古书零星记载,我国发明火药时(10世纪初),宫廷和民间使用一种蘸了硫磺的松木条点灯,名叫“发烛”。南宋临安(杭州)街头出售的“发烛”是蘸硫磺的松木片。明朝北京内城(西城)有卖劈柴的“劈柴胡同”和卖松木条的“取灯胡同”。有人据此认为是我国最早发明了火柴。其实,“发烛”和“取灯”都是易燃的引火柴,火种仍然来自火镰打火,还不是一擦就起火的现代火柴。
我国进入铁器时代(西汉),民间已普遍使用火镰打火。那么,两千年以后为什么仍然使用火镰打火呢?这真是封建社会“超长稳定”的可怕现象啊。中国的精英们“十年寒窗”苦读的“四书、五经”,并不提倡自然科学,科举考试也缺少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。明清两朝六万进士,二百多状元郎,不断充实北京的士大夫阶层,其中又有几位科学家呢?他们的府邸每晚都要点燃许多盏灯,出门打灯笼,就没想过改变复杂的“取灯”吗?直到清朝末年连续打败仗,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,中国人才如梦初醒,废科举,兴办现代学校,希望“科学救国”。
英国人沃克1826年发明了火柴,轻轻一划就起火,真方便呀。伦敦建立了火柴工厂,这小小精灵随着“日不落国”的商船队普及全球。来到北京,被称作“洋火”。待到我们有了自己的火柴厂,“洋火”才正名为火柴。
我是老资格烟民,对火柴情有独钟。您大概不会同情“有烟无火”的尴尬。电影也把烟民“对火”表现为“特务接头”。1976年夏夜唐山大地震,我从睡梦中惊醒,光脚跑到胡同里,什么也来不及拿,却下意识地从床头抓出来一盒香烟和火柴。余震不断,胡同里的邻居们都不敢回屋拿衣物。此时有烟民发现我蹲在老槐树下吸烟,佩服得五体投地,一个个上前伸手要烟,赞美之声不绝于耳:“老赵真神啦!”“光着膀子还有烟有火!”
改革开放后,火柴依然限量供应,一户一月5盒。定价偏低,2分钱一盒,“三十年一贯制”,工厂亏损,想涨一分钱,北京的市长讨论三年也不敢批准。我到上海、长沙、成都、广州写电影剧本,一律买不到火柴。1989年出国访问,我带回来的“新产品”,十几个一次性打火机,被朋友抢走一半。
中国人还是聪明的,乡镇企业模仿的能力极强,九十年代温州生产的一次性(电子)打火机价廉物美,畅销全球,占领世界市场百分之八十的份额。伦敦最后一家火柴厂关闭了——中国人“投桃报李”,用一次性打火机淘汰了火柴。
唉,风行全球的火柴何其短命耶?比起火镰打火,只是白驹过隙。若讲感悟,那就是我们正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。
人烟,这两个汉字组合得很妙——有人就有烟,“人烟稠密”还可形容市井繁华。现在变了,烟雾成为污染物。北京市民也从家家一炉火,取暖做饭烧开水,生火封火倒炉灰,迅速减少用火,主要用电。但若想一下,这些“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”的电灯、电话、电视、电脑、手机、空调、冰箱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电饭煲、洗衣机、热水器,虽然大多是“中国制造”,却不是“中国创造”。聪明的精英们赶紧投身“万众创新”的洪流吧,发展经济,要努力跨越模仿阶段。(文/ 赵大年)

新闻热点
新闻爆料